深山里的遠(yuǎn)古戰(zhàn)神后裔
在外人眼里,自豪地稱自己為血統(tǒng)“最正宗的苗族”的岜沙漢子,多少有些難以言表的另類———梳著用鐮刀剃成的怪異發(fā)式,一米多長(zhǎng)的老式火槍不離身,穿著如塑料薄膜般泛著紫光的藍(lán)靛麻布衣服,打扮極富象征意味。

世界上災(zāi)難深重而又頑強(qiáng)彪悍的民族中,猶太族和中國(guó)苗族的歷史都是由戰(zhàn)爭(zhēng)和遷徙寫(xiě)成的,如今,遍布全球的猶太人已然是世界公民,而苗族依然在黔東南的深山里延續(xù)著對(duì)祖先傳統(tǒng)的堅(jiān)守,《苗族古歌》唱道:“奶奶離東方,隊(duì)伍長(zhǎng)又長(zhǎng)……跋山又涉水,遷徙來(lái)西方……”從衣著、禁忌、信仰、農(nóng)耕、生產(chǎn)、愛(ài)情……山地民族有著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倚賴,他們別無(wú)選擇,自從祖先來(lái)到這里,他們的文化歸宿也在此扎根、繁衍,生生不息。
一件絕對(duì)嚴(yán)肅而莊重的事情
岜沙的一個(gè)明顯符號(hào)是“戶棍”,這是在中國(guó)所能見(jiàn)到的最古老的男性發(fā)式,也是岜沙男人除了火槍以外最重要的標(biāo)志。所謂“戶棍”,就是剃掉男性頭部 四周大部分的頭發(fā),僅留下頭頂中部的頭發(fā)并盤(pán)發(fā)為髻。岜沙男人成年之后,將終身保持這種據(jù)說(shuō)是蚩尤老祖宗時(shí)代傳下來(lái)的傳統(tǒng)發(fā)式。對(duì)于岜沙的男孩來(lái)說(shuō),洗頭、梳頭、剪發(fā)都是絕對(duì)嚴(yán)肅而莊重的事情,在他們十六歲接受接受一次名為“達(dá)給”古老成人禮時(shí),寨里的精神領(lǐng)袖———巫師,要用鐮刀,這或許聽(tīng)上去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工具將他們從小留起的一頭長(zhǎng)發(fā)剃去,僅僅保留中央的一撮。據(jù)說(shuō)如果外人要理這樣的發(fā)式需要20元人民幣,但相信除了岜沙人,沒(méi)有人會(huì)愿意將自己的腦袋當(dāng)麥地。
岜沙人認(rèn)為樹(shù)是祖先的靈魂,這些靈魂是需要被敬畏的。每一個(gè)岜沙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祖先的靈魂在現(xiàn)實(shí)世界和遠(yuǎn)古世界之間的互換,是靈魂和肉體在不同時(shí)空的交替。岜沙孩子出生后,父母會(huì)為他種下一棵樹(shù),這棵樹(shù)將伴隨著孩子成長(zhǎng)。如果這棵樹(shù)被風(fēng)刮倒或是被人砍掉,他們會(huì)認(rèn)為這是非常不吉利的預(yù)兆。當(dāng)一個(gè)人死去,就砍下代表他的那棵樹(shù),為他搭建起回到遠(yuǎn)古祖先那個(gè)世界的橋梁,同時(shí)在死者的墓地上栽種上另外一棵樹(shù),以示生命以另一種形式重新開(kāi)始。
執(zhí)著的樹(shù)木崇拜使岜沙人認(rèn)為,頭頂?shù)念^發(fā)就相當(dāng)于樹(shù)頂?shù)臉?shù)葉,樹(shù)頂?shù)娜~子如果全部落光,也就表示樹(shù)要死亡了。因此,頭頂?shù)陌l(fā)髻必須終生保留,不得損傷。完成一整套莊重的儀式之后,這留下的一撮長(zhǎng)發(fā)將被梳成高高的發(fā)髻,終身不得改變。這種頗有秦漢時(shí)期風(fēng)格的“戶棍”的發(fā)式顯示的是一種含蓄的雄性崇拜。
“岜沙人的槍是摘不下來(lái)的”
岜沙人深信自己是四十多個(gè)世紀(jì)前與漢族祖先黃帝爭(zhēng)奪中原大地統(tǒng)治權(quán)的古代苗族、瑤族部落聯(lián)盟的酋長(zhǎng)———蚩尤大帝的后裔。他們自豪地稱自己為血統(tǒng)“最正宗的苗族”,并認(rèn)為自己的祖先是蚩尤的第三個(gè)兒子。當(dāng)年蚩尤被黃帝打敗,率領(lǐng)自己的部落向西南偏遠(yuǎn)山地遷移,岜沙人的祖先就是大遷徙的先頭部隊(duì)九黎部落的一支。經(jīng)久的戰(zhàn)爭(zhēng)和遷徙使得這一支苗人對(duì)武器有著特別的渴望,他們要應(yīng)對(duì)強(qiáng)大的華夏部落的進(jìn)攻,要抵御大遷徙中遇到的猛獸,要給部落中的婦女和兒童獲取動(dòng)物蛋白……這就是為什么時(shí)至今日,岜沙村的男人依舊對(duì)火槍有著圖騰般的崇拜。
十六歲,對(duì)一個(gè)岜沙男子來(lái)說(shuō)是非常重要的時(shí)間,這不僅因?yàn)樵谶@個(gè)時(shí)候他們要接受“達(dá)給”成人禮,更重要的是,他們可以背槍了,他們的父親會(huì)親手為他們準(zhǔn)備好禮物———火槍,一個(gè)槍手的身份對(duì)于岜沙男人來(lái)說(shuō)才意味著真正成年,可以吹芒筒、可以跳花坡、可以游方……岜沙男人的槍其實(shí)是一種老式的,射程只有二十多米的簡(jiǎn)易火藥槍。在岜沙,如果能擁有祖父甚至太祖父留下來(lái)的老槍,是非常值得炫耀和自豪的事情,那是一種流淌在血液里的尚武情節(jié),有槍在,就有勇氣和力量。事實(shí)上,1949年以后,岜沙男人是被官方允許合法保留持槍傳統(tǒng)的惟一一支少數(shù)民族部落,槍圖騰對(duì)于現(xiàn)在的岜沙漢子來(lái)說(shuō)早已不是狩獵或防身這么簡(jiǎn)單的存在意義了。“一枝獵槍一條狗,一枝扛子朝山走。”岜沙村老支書(shū)易篤培說(shuō)“岜沙人的槍是摘不下來(lái)的”。直到今天,岜沙的男人們下田、看牛或上山拾柴,甚至上茅房都是依然槍不離身。
其實(shí),岜沙村的林子里早已沒(méi)有什么動(dòng)物可以獵取了,更多的時(shí)候,火槍的作用如同禮炮,用來(lái)歡迎來(lái)寨子參觀的游客。村民滾元亮是岜沙村的名人,確切的說(shuō),他和岜沙村都是被相機(jī)制造出來(lái)的“名人”,他的影像頻繁地出現(xiàn)在各種媒體上,幾乎成為了岜沙村的形象代言人。身高不過(guò)1米五的滾元亮目前的身份是村里的火槍表演隊(duì)隊(duì)長(zhǎng),也是最年輕的寨老。按照族里大寨老的“演義”,“滾元亮是岜沙先祖姜央的衛(wèi)士轉(zhuǎn)世,而岜沙男人的槍就是比照姜央的身高制作的,所以滾元亮長(zhǎng)到1米五就再也長(zhǎng)不上去嘞”。
岜沙村將接受一場(chǎng)“戰(zhàn)爭(zhēng)”
就在我們來(lái)到寨子的那天,他正帶領(lǐng)著他的兄弟們?cè)诖蹇诘奶J笙坪廣場(chǎng)上為五一長(zhǎng)假期間來(lái)村宅游玩的客人表演“槍手舞”,狹小的村道停滿了各地牌照的汽車,不倫不類的音樂(lè)在破舊且經(jīng)常卡殼的錄音機(jī)里彌漫開(kāi)來(lái),槍手們賣(mài)力地舞蹈贏得了不少掌聲。他們被游客到處拉著合影,而岜沙人原本不愿意讓外人拍照,怕把他們魂魄收進(jìn)機(jī)器里被帶走。考慮到游客的安全,原本朝天鳴槍的禮儀也被更換成了空槍扣扳機(jī),“意思到了就好了嘛”,火槍隊(duì)的隊(duì)員靦腆地解釋。寨子里多了農(nóng)家旅社和農(nóng)家飯店,也出現(xiàn)了常規(guī)旅游景點(diǎn)經(jīng)常可以看見(jiàn)的小商店,出售著制作低劣的各種紀(jì)念品。古老的岜沙村不可避免地將接受一場(chǎng)“戰(zhàn)爭(zhēng)”,一場(chǎng)自苗族大遷徙以來(lái)的,沒(méi)有硝煙和刀箭的戰(zhàn)爭(zhēng),像化石一樣不可再生的原生文化和傳統(tǒng),將不可避免地遭遇外來(lái)文明和價(jià)值觀的沖擊,他們被時(shí)代推上了一次精神和文化的遷徙之路。于此,我們可能無(wú)權(quán)評(píng)論什么,畢竟相機(jī)里的奇風(fēng)異俗對(duì)于原住民來(lái)說(shuō)也意味著沉甸甸的生活艱辛。
以前,岜沙女人的地位很低,大多沒(méi)有文化,甚至沒(méi)有自己的名字,她們甚至沒(méi)辦法自己收信件,留下的都是丈夫的名字。村子開(kāi)發(fā)旅游后,很多女人出去打工,回來(lái)后,牛仔褲代替了傳統(tǒng)的刺繡裙。滾元亮家的一面墻上貼的都是他的照片。他有著“非常岜沙”的外形,他去過(guò)黔東南州的首府凱里,去過(guò)首都北京,在岜沙,算是見(jiàn)過(guò)世面的能耐人,他把在天安門(mén)廣場(chǎng)上的留影貼在屋里最顯眼的位置。多數(shù)時(shí)間,他要帶領(lǐng)著村里的二十多個(gè)姑娘小伙,在蘆笙坪上為游客表演拜樹(shù)、“剃頭”、吹蘆笙、“火槍舞”……岜沙這座曾經(jīng)封閉在大山深處的苗族部落必將面臨著改變,當(dāng)一年一度的蘆笙節(jié)變成一天數(shù)次,當(dāng)火槍不再需要火藥觸發(fā),當(dāng)傳統(tǒng)成為經(jīng)濟(jì)的籌碼,當(dāng)世代傳承的古老文化依靠純粹而麻木的表演維系時(shí),古老的岜沙還有多少神秘可以待價(jià)而沽?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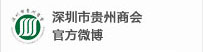



 深圳市貴州商會(huì)
深圳市貴州商會(huì)